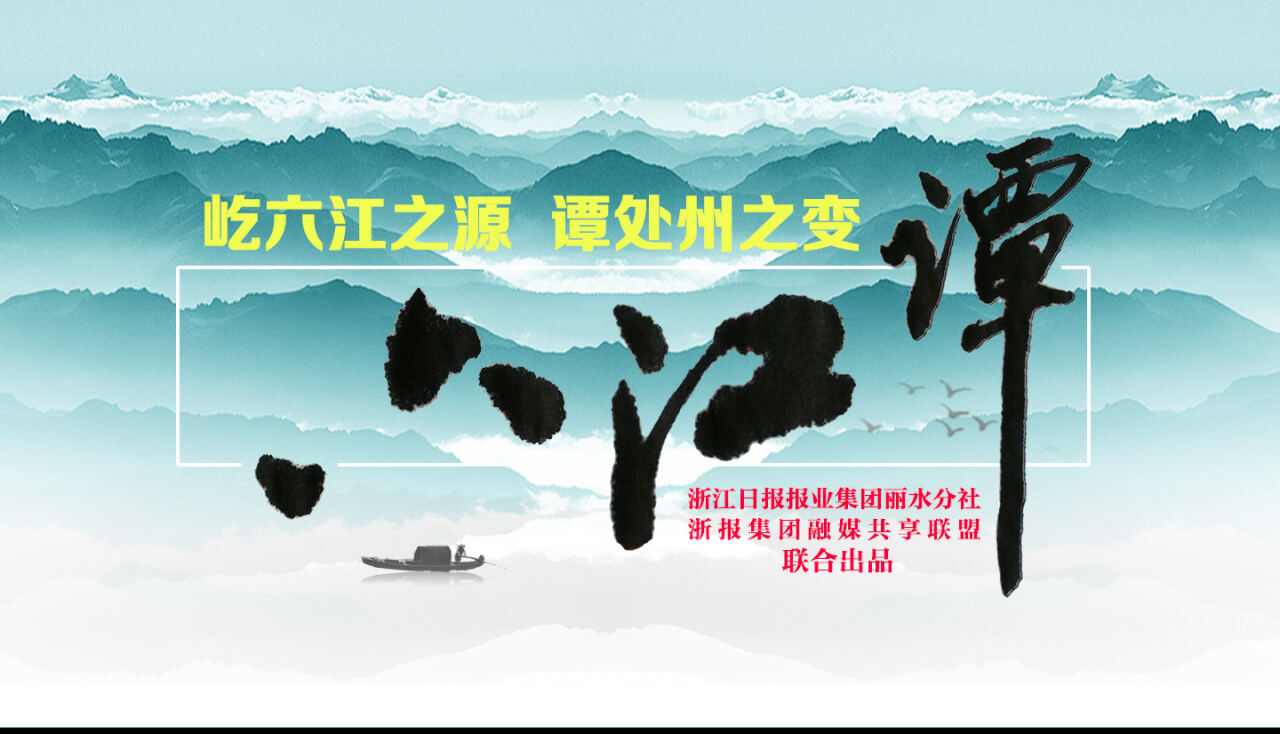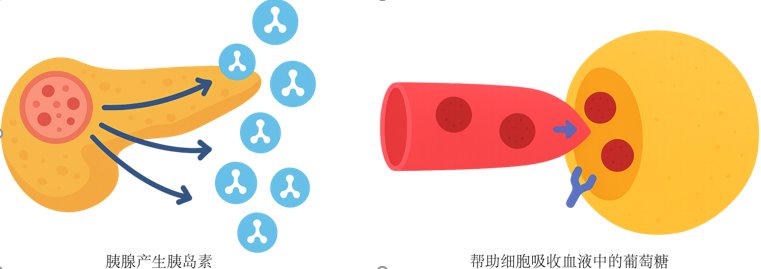与许多浮光掠影、闲情纵笔的思乡追忆不同,散文作者吴梅英突破传统经验的藩篱,以其亲身介入的方式,以其真诚的“非虚构式”笔触,带领读者重返现场,共同触摸城市化进程之下浙西南乡村那些被情感浸润得刻骨的遥远事物,共同窥探社会转型之下人与自然所面对的多重境遇。
故乡总是与大地、山川、田野、溪流、炊烟、母亲等人事景物紧密关联,农耕视域下的自然、民俗、人伦、亲情等,所负载的不仅有岁月的凝重,更多的则是作者对温暖生活的感知。《拾榧》《偷桃》《背树》《采茶》《砍柴》等等篇什,记录的是童年乡村生活自由、自洽的生活场景,作者以丰盈的细节描摹,对地地道道“原住民”的生活体态进行原汁原味的展现,让人深受感染、心向往之。《年味》《端午》等系列组章,作者则以亲历传统民俗的叙写,既传递出这一方小小土地上人们的生存常态和精神需要,又表达了对家乡熟稔于心的深情。民俗礼节可以说是农耕文明承载方式的一种,在广泛的乡土文化集成里,作者直面大家所熟知的“过年打尘”“接太公婆”“砍摇钱树”“包粽子”“插菖蒲”,让那些淹没于岁月烟尘里的习俗活动跃然纸面。那些漫不经心又适得其所的日常,在作者看来或许就是这些长居于此的村民们精神生活最好的补给。
作者吴梅英惯以“我”的视角,去看待龙南乡目所能及的一切,或触景生情、睹物思人;或他乡遥寄、午夜梦回。《老屋》瞬间让人置身于龙井溪上游的某个老院子里,杉木房梁壁板、天井、锅灶、屋外的石子路、桃树等意象的交叠,在治疗着自己“乡愁抑郁”的同时,更是对人们往昔怀念精神顾盼的共同提醒。《麻竹坑》一文则依旧站在主观的立场,去还原与祖母、与伯父、与姑婆等相关系的细小情节。无法割舍的血脉亲情在村庄的情景交互里,在“我”的情感流向里,因其细腻而可感,因其真实生辉。
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当下,乡土空间正在日益萎缩,传统的乡村生活已经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作者吴梅英也分明感受到这种“危机”的来临。乡村的命运、乡人的命运,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作者力图通过事件的记录来表现这种变革,并对命运遭遇背后的世事沧桑发出沉重的喟叹。她在《万寿菊》中这样写道:“……这些年,我也是跌跌撞撞地走。病痛让人过早熟悉无常,变得胆怯,有时近乎冷漠。但金炎,我是我想送他一程的。一个叫龙井的小村庄里,一个叫金炎的人,他活过……我见证这一切,我就是他曾经活过的证明。然而,除了记录,我还能做些什么呢?”那些朴素的、纯粹的,具有极强在场感的叙述里,一种无力感、焦灼感显得异常汹涌,故乡之所以“故”也霎时变得立体。
作者吴梅英总是不惜笔墨关注时代变奏之下,个体生命与山乡大地的血脉联系。“……一桌热腾腾的菜摆上了桌。一个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走进大会堂。不熟悉的,肯定是谁家的女婿或者媳妇,还有正在成长的孩子们。他们也许从来没有在这个村庄生活过,只在清明时节,被家人带了回来,看看这个本该属于他们的村庄。村庄正在老去,又似乎还年轻着。几百人的微信群里,节庆的氛围正被图片带出。”不可否认,发展更替所带来的村庄“空心”已成为一种常态,一代一代人对村庄渐生的陌生感也愈发强烈,“故乡”几近成为人们情感认知上的一个“地理符号”,这种境况从作者的叙述中得到证实。也正由此,我们不仅感受到作者对故土情之深、爱之切,更是捕捉到了乡土情怀遮蔽之下,那些独特的发现和直击灵魂的钝痛。
或许每个作家的书写,都与其原生故乡存在难以割舍的联系。故乡的山水自然、世故人情、变迁感怀为作家吴梅英提供了丰富的散文写作资源,也培养了她自然、灵动、敏感的文学气质。不论是写人、写事、写景、写物,处处透露着真诚、诗性,且赋予哲思,其散文的包容性使得她的叙事更加可靠、更具深度,也更彰显出潜藏的力量。
“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接近,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在当下乡土散文写作的语境中,吴梅英以回望记录的非虚构方式进行“纸上还乡”,以一己之力叙写着一个地域上厚重的人文生态,与其说是对乡风乡情的一次致意,不如说是多年来对故乡回探的情绪压制之下跨越“乡愁”的精神和鸣。
[作者简介]
叶琛,1986年生,浙江庆元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丽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首批浙江省“新荷计划”人才库人才、丽水市第一批“绿谷英才”特殊支持计划人才文艺人才。曾获浙江省作协新荷文丛项目扶持、浙江省文学期刊创作成果奖、闻一多诗歌奖提名奖。现任丽水市中心医院党建办负责人,兼任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