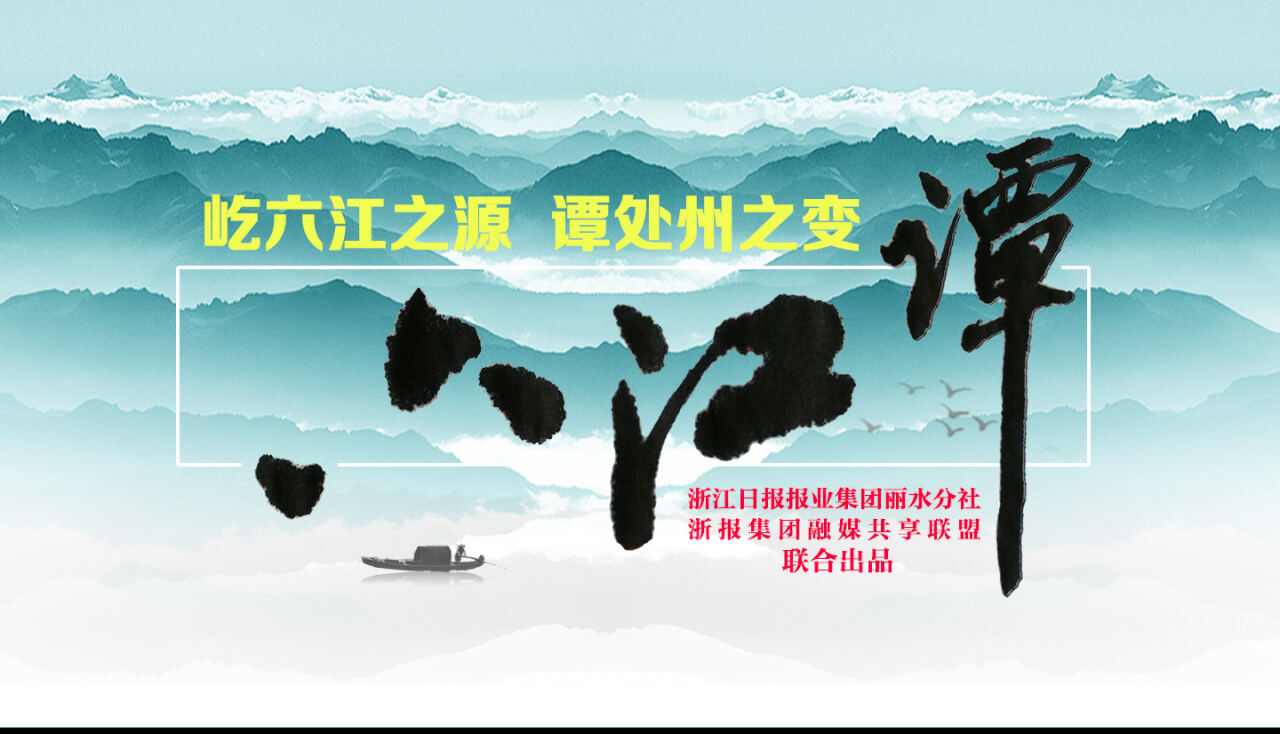毋庸讳言,作为新近崛起青年诗人,叶琛熟谙“写诗之道”,他试图穿越语言的迷雾,从个体的我出发,洞悉那被遮蔽的世界。他从主体困境中不断地逃离,凭“想象力”和“制造幻觉”突围,在现代性的生活语境中,努力保持着个体的“纯洁”。他的诗是纯净的,是充满幻觉的,是乌托邦式的,在这里,诗人选择摒弃世俗的生活场域,在意识世界的语言之邦,体悟出一条自我的生存之道。
叶琛是西西弗斯式的诗人,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审美坚守,远离当下流行风尚的诗歌写作,这是一位优秀诗人内心的一份执念,亦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胸怀与气魄。他的诗,灵气大于才气,才气大于技艺,隐藏在诗背后的那种精神境界,不仅体现出一位诗人的天赋和才智,也看得出一位诗人的诗学追求。在英国著名批评家T.S.艾略特看来,“诗人在任何程度上的卓越或有趣,并不在于他个人的感情,不在于那些被他生活中某些特殊事件所唤起的感情,他的人、个人感情可能很简单、粗糙,或者乏味,他诗歌中的感情却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但是它的复杂性并不是那些在生活中具有非常复杂或异常的感情的人们所具有的感情复杂性。”在这里,诗人并不一定非要去寻找新的感情和经验,而是在惯常的经验与感情中开拓出属于“自我”的诗意。诗人将个体经验集中起来,经过有意识地对词语和感情的加工,让那些沉睡的事物苏醒过来。“这些阳台上晾晒的衣服\交出原有的潮湿、重量,沉迷于虚无冥想”“宽广的蓝掠过大地\包围了此时租所和租所里面\全部的生活迹象\有时候,这些痕迹是短暂的\也有的时候,它们的消逝像是时光的买卖”。这首《午后》将感叹“时光易逝”的个体情感融入诗中,个体的关怀转化为普适性的价值,既拔高了诗的境界,也提升了诗的品格。尤其是“它们的消逝像是时光的买卖”从虚无回到现实,似真似幻的场景,为我们洞悉了另一种可能性、一种疑问——商品时代还有什么不可以买卖?这富有新意且饱含着人文关怀式的思考,让人自然而然地进入到诗人话语之境。
“自然之物随性静美\茎叶的伸展像是我们密谈中词语的交换\对于世事,那些茂盛的应该比我们\靠得更近\我学着母亲去摘掉粘手的腐叶\植物代谢所建立的新生秩序\让这个下午\变得格外开阔”。(选自《菜地手记》) “雪落在枝桠上\纷纷扬扬\每一片都在叠加\每一片都有对应,孤独、彷徨\以及鲜为人知的拆解\寒风鼓吹,而我们都不说话\雪夜的冷衬出无限唏嘘的人与事”。(选自《深雪》)叶琛的诗歌中到处充溢着情感与灵感,那些“孤独”“彷徨”“悲伤”等等便是情感的映照,而那些看似信手拈来的句子,便是灵感的迸发,但他又不断地尝试着去打破常规的情感逻辑,以期在词语的律动中找到那个属于“原初状态”的“我”。他在词语的自我调适中,捕获灵感,那些原发性的意象,不断地引导我们朝向虚无、朝向幻觉,呈现出一种内心的焦虑和自我的救赎的悬浮状态,并在此状态下洞悉存在的要义。
“时间速朽\我在年轮里告别、忏悔、贴幸福的标签\我在虚构中\完成又一个满意的悲伤\风吹浮世\什么正填充着寒水湾通幽的未尽之路\而我,反复模仿另一段\似曾相识的人生”。(选自《寒水湾记事》)什么是满意的悲伤?什么是似曾相识的人生?从叶琛的诗中,我们隐约看到一个诗人的充满谜语式、不知从何而来的悖论式的经验感知,或许正是这种悖论,让那些看似自我封闭的诗渐渐敞开,于是所有新的或者可能性的解释,便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尤其是那些深陷时间迷局的意象,在一众并不成型的想象中,完成了自我的塑身。或许,正是由于叶琛的这种非比寻常的内在思维,才引发了诗人对自我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和读者对其作品的阅读兴趣,总想跟着他去一探究竟。之于读者而言,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与作者产生共情,只有在共情的状态下,才能从作品中获悉作品内部所隐含的美学旨趣和审美价值,才能直抵诗的内部获得隐喻之根。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断地试着要和诗人达成一致,并力求走进他的心灵世界,想看看他诗歌背后那个隐藏的世界。雪莱在《为诗一辩》中曾经指出,“诗歌可以揭起隐藏的世界之美的面纱。”这里的诗歌是朝向真实、朝向本真世界的,那些被遮蔽的事物,终将在诗的解蔽之下,向我们敞开。“并非要冬天的早晨\才会有霜,在一个词里,在一截想象中\细盐引导冷不断深入,深入\然后于万物之肤涂上粒性的白锈\这寂静仿佛新生\这柔软仿佛曝晒的被褥,窗台上\一朵郁金香开放的动机\忽然间就被阳光照得格外通亮\……我手持书本,对一句话的复诵\像是一场思维运算:人这一生\到底有多少哽咽的沙粒在屋顶悄悄滑落”。(选自《霜重》)“你说,心怀远方就不孤独了\为此,我沿着季节的青草地\走了很远\你说,在逃离中你像一截\欢快的小水流\我忽然少了一种\应对的方式\郊野之外,我并没有让你发现\一个灵魂\正走在钟声消失的边界 ”。(选自《郊外的钟声》)诗人笔下的事物,如此的安静,如此的美,如此的惹人怜爱,如此的令人亲近,在他构建的诗意国度里,“我”是一个固定的、永恒的形式的存在,“我”是一个自然的“我”,也是一个哲学的“我”,“我”既是“孤寂处所的灵魂”,又是“时空统一的玄思者”,所以才会有了“我手持书本,对一句话的复诵”。“正走在钟声消失的边界”这个边界在何处,留给我的门的便是一种不可释的想象空间,或许正是这趋向于无穷、无尽的事物,才真正地让人感动,才能释放出无限的艺术魅力和艺术之美。
波德莱尔在《浪漫派的艺术》一书中曾提出过这样的命题,“坏诗人是那些人,他们程式化。”程式化写作是当下诗歌写作的一个极大弊端,同质化的诗歌拉低了人类的审美,也让诗歌陷入了一种令人作呕的尴尬之境。但是,好的诗歌作品,仍然是可以使神灵在人的内心驻留,可以让读者在其中找到灵魂的共通之处。在叶琛的诗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他一直在坚守内心的那份宁静——颇具新古典主义色彩的宁静。“这是城市的余音\我喜欢这条被舍弃的声线。悠远\穿过尘嚣外的寂静”。(选自《郊外的钟声》)“寒风鼓吹,而我们都不说话\雪夜的冷衬出无限唏嘘的人与事”。(选自《深雪》)“夜露凉\寒水湾无风也无浪\厌倦说话,那就坐一会吧\看一看\水边的芦苇空荡荡的\水边的卑微还原体内\水边的孤独错落有致”。(选自《寒水湾记事》)“近乎幻觉\瓷器、绸缎,静若处子\轻盈之物取出的一部分储藏”。(选自《夜空》)“这个下午,缄默接替了回首\我怀抱乌有\趴在窗口远眺\神秘的快乐,以一阵清风回应”。(选自《午后》)在这组诗中写“宁静”的诗句远不止这些,我们不再一一举隅。诗人切入宁静的角度有多种,这也给他的诗带来了更多可释的空间。他的宁静可以是在城市的喧嚣中寻觅,可以是在众生沉默中反衬,可以是在空寂孤独之中回应,可以是在幻觉玄妙之中乍现,也可以是在蓦然回首中清风对语,无论哪种切入方式都带有鲜明地古典意味,值得关注。这些关于“宁静”的不同书写,虽然有着同一指向,但却没有陷入同质化的尴尬之中。而且,纵观其诗,我们能发现,诗人一直在寻找他自己定义的“现实”,这种具有超拔意义的“现实”恰恰是他的立足之本,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有意识的打破某种幻觉,让其抒情的线条变得模糊,多义,不知不觉中便将我们带入他事先建构的场域之内。
叶琛的诸多诗篇,均以日常观察为切口,以平平之态书写午后闲暇时光的惬意,寻找生命归宿的泰然,喟叹时光易逝的无可奈何……这是他与周遭事物对话的方式,这也是一位诗人柔软、温润、厚重与沉潜的另一个截面。他在虚无之中,下意识地以其微弱之力打破幻觉,那些敞开的诗便缓缓走来。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诗人叶琛的诗写之路,会因其敏感、热爱与敬畏而走得更加阔达、持远。
[评论家简介]
敬笃,文学博士、青年诗人、批评家。作品散见于《星星》《扬子江诗刊》《诗探索》《文学报》《山东文学》《延河》等期刊,获奖若干。出版诗集《凋谢的孤独》。